时间:2023-09-07 00:11点击:676
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转型
——兼析杨春时《中国文化转型》一书的几点失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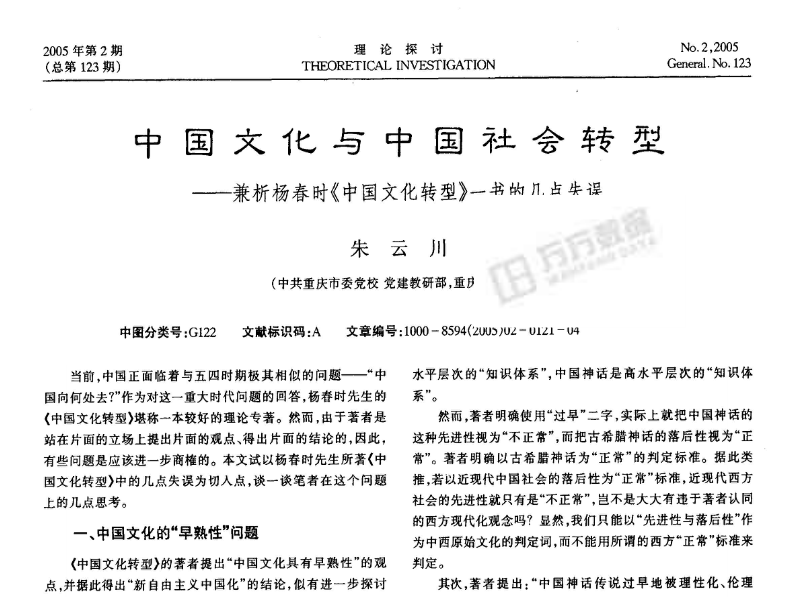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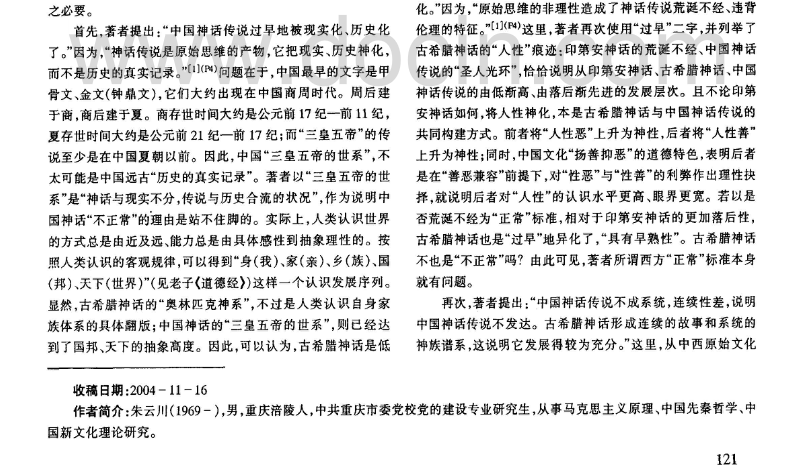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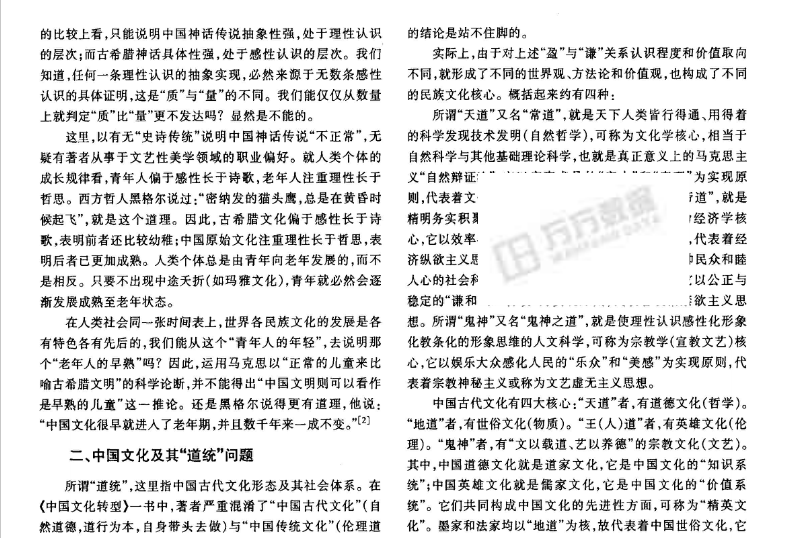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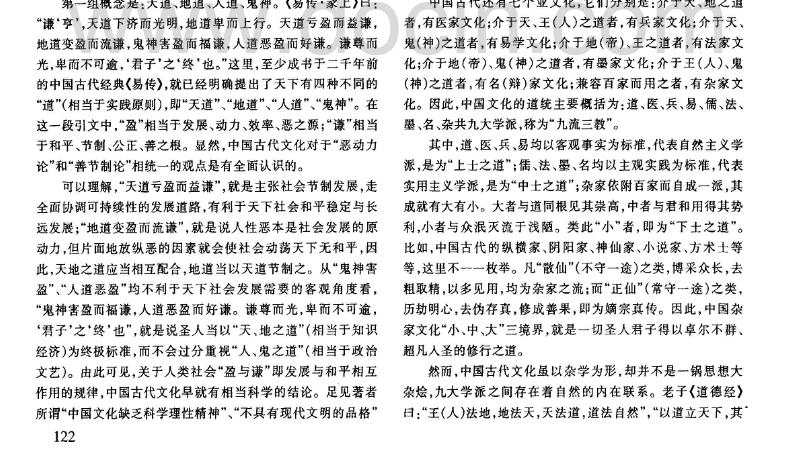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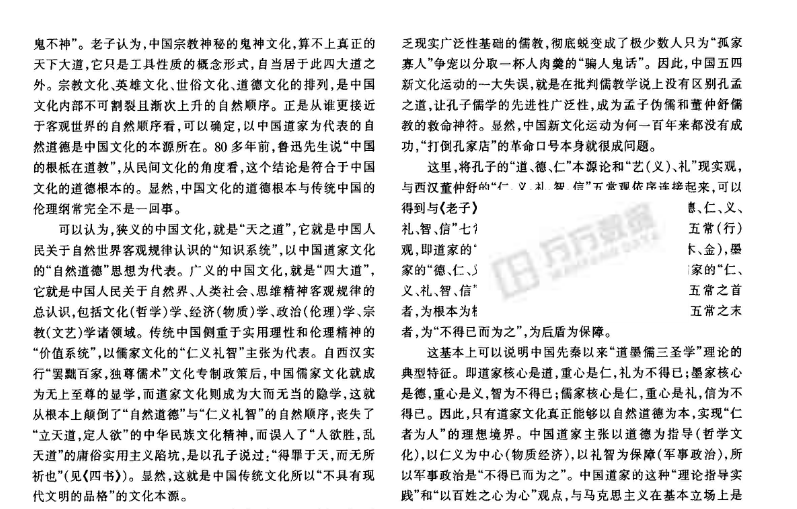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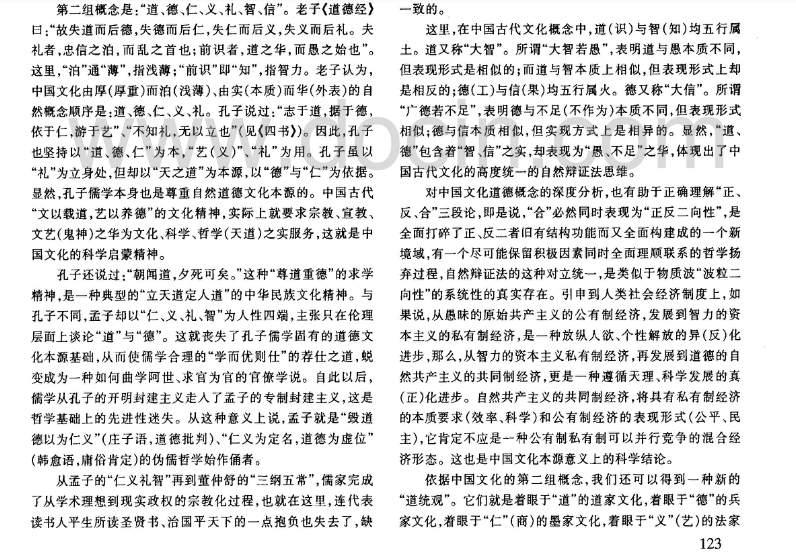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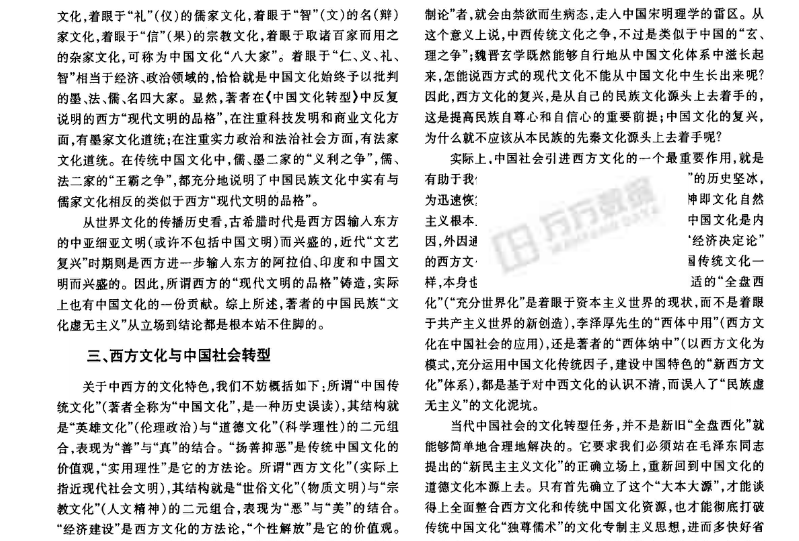

原标题:
关于杨春时《中国文化转型》几点失误
——兼析中国新自由主义者的民族虚无主义悖谬
朱云川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自由主义中国化,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两大思潮。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选择,居于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然而,自由主义思潮并不甘心这种历史的失败,目前它正企图以新自由主义中国化的形式卷土重来。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原理,深入批判新自由主义错误思潮,是我们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当前,我们中国正面临着与五四时期极其相似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作为对这一重大时代问题的回答,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左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共产主义社会道路;一种是右翼的“新自由主义中国化”,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前者是正确的,后者是错误的,关于这一点早有结论,似乎不必多说。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目前后者似有卷土重来的某种势头,因而很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在目前国内较多的新自由主义论著中,杨春时先生《中国文化转型》这本书因为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而堪称其代表。因此,实事求是地科学分析该书主要观点的理论失误,是我们有力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可行途径。文中不妥之处,敬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中国原始文化的“早熟性”问题
在当代中国理论严重滞后于实践的现状中,公道地说,《中国文化转型》算是一本较好的理论专著,“文化转型问题”的确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然而,由于著者仅仅着眼于使中国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具体手段,而忘记了从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总体目标上去把握全局,因而站在片面的立场上提出了错误的观点、得出了有害的结论。就中国文化转型问题而言,著者站在中国文化“民族虚无主义”的片面立场上,提出了“中国文化具有早熟性”的错误观点,最后得出了“新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有害结论。是以很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关于“中国文化具有早熟性”的观点,实际上是著者一系列主观性标准陆续炮制出来的。仅以著者对中国神话传说三大特征的论述为例说明之。
首先,著者提出:“第一,中国神话传说过早地被现实化、历史化了。”因为,“神话传说是原始思维的产物,它把现实、历史神化,而不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该书第4页)问题在于,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金文(钟鼎文),它们大约出现在中国商周时代。周后于商,商后于夏。商朝存世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十七纪——前十一纪,夏朝存世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二十一纪——前十七纪;而“三皇五帝”的传说至少是在中国夏朝以前。因此,中国“三皇五帝的世系”,不太可能是中国远古“历史的真实记录”。著者以“三皇五帝的世系”是“神话与现实不分,传说与历史合流的状况”,作为说明中国神话“不正常”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实际上,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总是由近及远、能力总是由具体感性到抽象理性的。按照人类认识的客观规律,我们可以得到“身、家、乡(族)、国(邦)、天下(世界)”这样一个认识发展序列。显然,古希腊神话的“奥林匹克神系”,不过是人类认识自身家族体系的具体翻版;中国神话的“三皇五帝的世系”,则已经达到了国邦、天下的抽象高度。因此,古希腊神话是低水平层次 的“知识体系”,中国神话是高水平层次的“知识体系”。
然而,著者明确使用了“过早”二字,实际上就把中国神话的这种先进性视为“不正常”,而把古希腊神话的落后性视为“正常”。著者明确以古希腊神话为“正常”的判定标准。据此类推,若以“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落后性为“正常”标准,“近现代”西方社会的先进性就只有是“不正常”,岂不是大大有违于著者鼓吹的现代化观念吗?显然,我们只有以“先进性与落后性”作为中西原始文化的判定词,而不能用所谓的西方“正常”标准。
其次,著者提出:“第二,中国神话传说过早地被理性化、伦理化。”因为,“原始思维的非理性造成了神话传说荒诞不经、违背伦理的特征。”(该书第4页)这里,著者再次使用了“过早”二字。著者列举了古希腊神话的“人性”痕迹:印第安神话的荒诞不经、中国神话传说的“圣人光环”,恰恰说明了从印第安神话、古希腊神话、中国神话传说的由低渐高、由落后渐先进的发展层次。且不论印第安神话如何,将“人性”神化,本是古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传说的共同构建方法。前者将“人性恶”上升为神性,后者将“人性善”上升为神性;同时,中国文化“扬善抑恶”的道德特色,表明了后者是在“善恶兼容”的前提下,对“性恶”与“性善”的利弊作出了理性抉择,就说明了后者对“人性”的认识水平更高、眼界更宽。倘若以是否“荒谬不经”为“正常”标准,相对于印第安神话的更加落后性,古希腊神话也“过早”地异化了,“具有早熟性”。古希腊神话不也是“不正常”吗?由此可见,著者的所谓“正常”标准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还应指出,著者说“古希腊神话把神人化,中国神话则把人神化”的概括,与前文的“神话传说是原始思维的产物,它把现实、历史神话”在逻辑上是难以自洽的。人类社会的现实经验告诉我们,地球上先有人类社会然后才有神话,把万物(包括人)神化是远古神话传说的唯一可靠来源。因此,说中国神话“把人神化”没有错,但说古希腊神话“把神人化”,岂不是说古希腊先有神祗而后方有人类社会吗?这种“神”先于“人”的观点,除了表明著者的西方式“有神论”宗教文化痕迹外,还能有别的合理解释吗?实际上,如同中国古代的墨家学派一样,这种“有神论”痕迹,就是其致命病根所在。
最后,著者提出:“第三,中国神话传说不成系统,连续性差,说明中国神话传说不发达。古希腊神话形成连续的故事和系统的神族谱系,这说明它发展得较为充分。”这里,中西原始文化的比较,只有说明中国神话传说抽象性强,处于理性认识的高水平层次;而古希腊神话具体性强,处于感性认识的低水平层次。我们知道,一条理性认识的抽象,必然来源于无数条感性认识的具体证明,这是“质”与“量”的不同。我们能仅从数量上去判定“质”比“量”更不发达吗?显然是不能的。
这里,以有无“史诗传统”来说明中国神话传说“不正常”,无疑有著者从事于文艺性美学领域的特殊偏好。就人类个体的成长规律看,青年人偏于感性长于诗歌,老年人注重理性长于哲思。西方大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密纳发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候起飞”,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古希腊文化偏于感性长于诗歌,表明前者还比较幼稚;中国原始文化注重理性长于哲思,表明后者已更加成熟。人类个体总是由青年向老年发展的,而不是相反。只要不出现中途夭折(如玛雅文化),青年就必然会逐渐发展成熟至老年状态。感性的最终发展是死亡(不断新生),理性的最终发展是永恒(真理永恒)。因此,老年型文化必有其青年时期,而青年型文化未必能有其老年时期。
在人类同一张时间表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各有特色和先后的,我们能从这个“青年人的年轻”,去说明那个“老年人的早熟”吗?因此,运用马克思以“正常的儿童来比喻古希腊文明”的科学论断,并不能得出“中国文明则可以看作是早熟的儿童”这一推论。还是黑格尔的话更有道理,他说:“中国文化很早就进入了老年期,并且数千年来一成不变。”这就是从哲学理性的终极永恒意义上说的。关于这种真理永恒性的证明,由以《老子》为代表的中国道家文化思想中可以得到。
二、中国文化及其“道统”问题
在《中国文化转型》一书中,著者严重混淆了“中国文化”(以道家精神为本)与“传统中国文化”(以儒教特色为用)两个文化概念,而犯了以末梢指代根本的重大概念失误。这里,仅就与中国文化源头有关的两组概念分析说明之。
第一组概念是:“天道”、“地道”、“人道”、“鬼神”。
《易传.彖上》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这里,“盈”相当于发展、动力、效率、恶之源,“谦”相当于和平、节制、公正、善之根。显然,真正的中国文化源头对于“恶动力论”和“善崇高论”相统一的观点是有全面认识的。
天道“亏盈而益谦”,就是主张节制发展、走世界可持续性发展道路,这有利于天下社会的和平稳定和长远发展;地道“变盈而流谦”,就是说“恶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但片面地“纵恶”就会使社会出现动荡天下失去稳定,因此地道经济当以天道文化(理论)节制之。圣人君子应当以“天地之道”(知识经济)为终极标准,而不会过分重视“人鬼之道”(政治文艺)。这是从“鬼神害盈”、“人道恶盈”两者不利于天下社会发展和进步需要的客观角度说的。由此可见,关于“和平”与“发展”的相互作用规律,中国古代文化早有科学的结论。足见著者所谓“中国文化缺乏科学理性精神”、“不具有现代文明的品格”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实际上,由于人们对上述“盈”与“谦”关系的认识和态度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也就是不同的民族核心文化。概括起来大约有四种:
“天道”就是天下人皆能行得通、用得着的自然科学道理,可称为文化(理论)学,相当于自然科学与其他基础理论科学,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它以实事求是的“中”和“真”为实现原则,代表着文化自然主义思想。“地道”又名“帝道”,就是精明务实积聚财富的社会科学道理(经济基础),可称为经济学,它以效率与发展的“盈”和“恶”为实现原则,代表着经济纵欲主义思想。“人道”又名“王道”,就是统帅民众和睦人心的社会科学道理(上层建筑),可称为政治学,它以公正与稳定的“谦”和“善”为实现原则,代表着政治禁欲主义思想。“鬼神”就是使理性认识感性化形象化教条化的形象思维的人文科学道理,可称为文艺(宗教)学,它以娱乐大众感化人民的“乐”和“美”为实现原则,代表着文艺虚无主义思想。
实际上,中国有四大核心(大)文化:以“天道”为核心者,有中国道德(科学理性)文化。以“地道”为核心者,有中国世俗(物质)文化。以“王(人)道”为核心者,有中国英雄(伦理)文化。以“鬼神”为核心者,有中国“文以载道、艺以养德”的宗教艺术文化。其中,中国道德文化就是真正的道家文化,它是中国文化的“知识系统”;中国英雄文化就是真正的儒家文化,它是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它们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先进性方面,可称为“精英文化”。墨家文化和法家文化均以“地道”为核心,故代表着中国世俗文化,它们与现代西方文化思想是很相似的;名家文化(一般文艺知识分子)和佛家文化(宗教文艺知识分子)均以“鬼神”为核心,故代表着中国宗教文化。它们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广泛性方面,可称为“民间文化”。
具体地说,中国还有七个亚文化,它们分别是:介于天、地之道者,有中国医家文化;介于天、王(人)之道者,有中国兵家文化;介于天、鬼(神)之道者,有中国易学文化;介于地(帝)、王之道者,有中国法家文化;介于地(帝)、鬼(神)之道者,有中国墨家文化;介于王(人)、鬼(神)之道者,有中国名(辩)家文化;兼容“百家”而用之者,有中国杂家文化。因此,我们可以将中国文化系统主要概括成:道、医、兵、易、儒、法、墨、名、杂共九大学派,称为“九流三教”。其中,道、医、兵、易四大家代表自然主义学派,号称“上士之道”;儒、法、墨、名四大家代表实用主义学派,号称“中士之道”;杂家依附于“百家”而又自成一派,其成就有大有小。“大”者与道家同根与圣人相齐,“中”者与儒家同用与君子相平,“小”者则与世间众人无别流于浅陋无知也。比如,中国古代的纵横家、阴阳家、神仙家、小说家、方术士等等,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因此,中国杂家文化的“小、中、大”三境界,实际上就是古今中外一切圣人君子之所以“卓越不群、超凡入圣”的道德文化修养之道。
中国文化并不是一锅思想大杂烩,九大学派(道统)之间是有其自然的内在联系的。《老子》曰:“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神”。老子认为,中国宗教文化算不上真正的“大道”,它只能是工具性质的东西,自当居于末位。由中国宗教文化、中国英雄文化、中国世俗文化、中国道德文化的排列,是中国文化内部不可割裂且渐次上升的自然顺序。正是从更加接近于客观世界的这一自然顺序看,我们才说道德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本源所在。八十多年前,鲁迅先生说“中国的根柢在道教”,从民间文化的角度看,这个结论是符合于中国文化的道德根本的。中国文化的道德文化根本与传统中国的伦理文化特色原本是两回事。
因此,狭义的中国文化,就是“天之道”,它就是中国人民关于自然世界客观规律认识的“知识系统”,可以中国道家文化的“自然道德”思想为代表。广义的中国文化,就是“四大道”,它就是中国人民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精神客观规律的总认识,包括文化(理论)学、经济学、政治学、文艺(宗教)学诸领域。传统中国侧重于实用理性和伦理精神的“价值系统”,可以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主张为代表。自中国西汉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以后,儒家文化就成为无上至尊的显学,道家文化则成为压抑无用的隐学,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自然道德”与“仁义礼智”的客观顺序,丧失了“立天之道,以定人矣”的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而误入了孔子所谓的“得罪于天,而无所祈也”的庸俗实用主义陷坑。显然,这就是传统中国文化之所以“不具有现代文明的品格”的根本原因。
第二组概念是:“道、德、仁、义、礼、智、信”。
《老子》曰:“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老子认为,中国文化由厚而泊、由实而华的自然概念顺序是:道、德、仁、义、礼、前识(知)。孔子说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不知礼,无以立也”。因此,孔子也是坚持以“道、德、仁”为本,“艺(信)”、“礼”为用的。孔子虽然以“礼”为立身处,但却是以“天之道”为本源,以“德”与“仁”为依据的。孔子还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这种尊道重德的精神,是一种典型的“以天道定人道”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与孔子不同,孟子却是以“仁、义、礼、智”为人性四端,主张在伦理文化层次上谈论“道”与“德”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孟子就是“毁道德以为仁义”(庄子语)、“仁义为定名,道德为虚位”(韩愈语)后儒哲学的始作蛹者。
这里,将孔子的“道、德、仁”本源论,与西汉董仲舒的“仁、义、礼、智、信”五常观依次连接起来,就可以得到与《老子》思想相同的“道、德、仁、义、礼、智、信”的七常观。这个“七常观”实际上包含着三大“五常(行)观”,它们分别是中国道家的“道、德、仁、义、礼”(土、火、水、木、金)五常观,中国墨家的“德、仁、义、礼、智”(火、水、木、金、土)五常观,中国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水、木、金、土、火)五常观。其中,居于五常之首者,为根本为指导核心;居于五常之中者,为实用为服务重心;居于五常之末者,为“不得已而为之”,为后盾为社会保障。因此,道家的重心是“仁”,墨家的重心是“义”,儒家的重心是“礼”。只有中国道家文化才能真正实现“仁者为人”的理想境界。中国道家主张以道德文化为指导,以仁义经济为中心,以礼智政治为保障,所以说政治军事是“不得已而为之”。中国道家的这种“理论指导实践”和“为天下百姓服务”的观点,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基本立场上是一致的。
这里,道(识)与智(知、文)均属于五行之“土”,德(工)与信(技、艺)均属于五行之“火”。道又可称为“大智”,所谓“大智若愚”,表明它与“智”在表现形式上是相反的;德又可称为“大信”,所谓“大匠无法”,表明它与“信”在实现方式上是相异的。因此,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艺以养德”文化精神,实际上就是要求宗教文艺(鬼神)为文化理论(天之道)服务,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科学启蒙精神。至于传统中国的“皮毛论”,即文艺专为政治服务的观点,不过是孟子后儒哲学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的历史反映而已,它与包括孔子思想在内的中国文化的科学启蒙精神是完全两样的。
依据中国文化的第二组概念,我们还可以得到一种新的“道统观”。它们就是着眼于“道”(大智)的道家文化,着眼于“德”(大信)的兵家文化,着眼于“仁”(商)的墨家文化,着眼于“义”(法)的法家文化,着眼于“礼”(仪)的儒家文化,着眼于“智”(文)的名(辩)家文化,着眼于“信”(艺)的宗教文化,着眼于取“百家”而用之的杂家文化,可称为中国文化“八大家”。着眼于“仁、义、礼、智”(相当于经济政治领域)的,恰恰就是中国道德文化始终予以大力批判的“墨、法、儒、名”四大家。显然,著者在《中国文化转型》中反复说明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品格”,在注重科技发明和商业文化方面,有中国墨家文化道统;在注重实力政治和法治社会方面,有中国法家文化道统。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儒、墨二家的“义利之争”,儒、法二家的“王霸之争”,都充分地说明了中国民族文化中实有与儒家文化相反的“现代文明的品格”。
从世界文化的传播历史看,古希腊时代是西方因输入东方的中亚细亚文明(第一次不包括中国文明)而兴盛的,近代“文艺复兴”时期则是西方因进一步输入东方的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而兴盛的。因此,所谓西方的“现代文明的品格”铸造,实际上也有中国文化的一份贡献。综上所述,著者的中国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从立场到结论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三、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转型
仅就著者在《中国文化转型》中论及的文化特色,我们不妨概括如下:所谓“传统中国文化”(著者全称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历史误读),其结构就是“英雄文化”(伦理政治)与“道德文化”(科学理性)的二元组合,表现为“善”与“真”的结合。“扬善抑恶”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实用理性”是它的方法论。所谓“西方文化”(实际上指近现代社会文明),其结构就是“世俗文化”(物质文明)与“宗教文化”(人文精神)的二元组合,表现为“恶”与“美”的结合。“经济建设”是西方文化的方法论,“个性解放”是它的价值观。单纯就此而言,“善+真”的传统中国文化,与“恶+美”的西方文化的确不具有相通相同之处。
或许正因为如此,著者才断言道:“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现代文明的品格,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改造,它不会自行转化为现代文化,中国社会也不会自行进入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要进入近现代社会,只有引进外来文化即西方文化,舍此别无他途。”(该书第21—22页)应当说,著者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化基本特色的认识是正确的,但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
具体地说,近现代西方文化的科技意识、民主意识、重利意识、管理(贤者)意识、宗教意识、“仁”商文化等特点,可以由中国墨家文化中发掘出来;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帝王模式、殖民主义、强权政治、法治意识、富民强兵、人性本恶等特点,可以由中国法家文化中发掘出来。在中国先秦时代,墨家尚民主,儒家尚专制;墨家讲兼爱,儒家讲有别;法家尚法治,儒家尚人治;法家讲性恶,儒家讲性善。如此等等,都充分说明了中西方传统文化上的两极对立,进而也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无限丰富和博大精深。
实际上,贯穿着“天、地、王(人)、鬼神”四大道和“道、德、仁、义、礼、智、信”七常观的中国文化,本是一种万源归流、万水归渊的江海型世界大文化。仅以中国道家文化为证,它一方面是情理兼备、善恶兼容,另一方面又是厚理薄情、扬善抑恶。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内在统一的。如果彼此割裂各执一端,倡“个性解放”从“恶发展论”者,就会由纵欲而生恶俗,走入中国魏晋玄学的泥坑;倡“弘扬天理”从“善和平论”者,就会由禁欲而生病态,走入中国宋明理学的雷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西传统文化之争,不过是类似于中国文化内部的“玄、理之争”;魏晋玄学既然能够自行地从中国文化体系中滋长起来,怎么能说西方式的现代文化不能从中国文化内部生长出来呢?因此,西方文化的复兴,是从自己的民族文化源头上去着手的,这是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重要前提;中国文化的复兴,为什么就不应该从本民族的先秦文化源头上去着手呢?
实际上,中国社会引进西方文化的一个最重要作用,就是有助于我们彻底打破传统中国文化的“独尊儒术”的历史坚冰,为迅速恢复到中国道德文化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即文化自然主义根本上创造了现实条件。西方文化是外因,中国文化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但是,片面着眼于“经济决定论”的西方文化,与片面着眼于“政治决定论”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样,本身也是不能尽善尽美的。显然,无论是胡适的“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是着眼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现状,而不是着眼于共产主义世界的新创造),李泽厚先生的“西体中用”(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应用),还是著者的“西体纳中”(以西方文化为模式,充分运用中国文化传统因子,建设中国特色的“新西方文化”体系),都是基于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不清,而误入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殖民主义文化泥坑。
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任务,并不是新旧“全盘西化”就能够简单地合理地解决的。它要求我们必须站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新民主文化”正确立场上,重新回到中国文化的道德文化本源上去。只有首先确立了这个“大本大源”,才能谈得上全面整合西方文化和传统中国文化资源,也才能彻底打破传统中国文化“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思想,进而多快好省地建成符合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中国新民主文化。这就要求我们真正弘扬起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立足于中国道家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既要反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政治决定论”的英雄文化历史格局(以中国理学为代表),又要反对西方文化的“经济决定论”的世俗文化发展歧途(以中国玄学为代表)。因为,前者在强调圣人君子的先进性、合理性要求的同时,拒绝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性、合法性要求;后者则恰恰相反。
因此,我们必须把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立场,科学地确立在中国民族文化的自然道德根本上,形成这样一个世界大文化格局,它就是中国道德文化(科学理性)和英雄文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性要求,同中国世俗文化(经济建设)和宗教文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广泛性要求有机统一起来;坚持“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文化自然主义发展观,充分整合传统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有效资源,彻底打破两者业已形成的“政治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历史坚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立场,在当代中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理论创新)和共产主义全面可持续性发展理论指导下,真正建立起“反帝”(经济决定论)“反封建”(政治决定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新民主文化。
总之,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对新文化革命中的种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实用主义、割裂主义、庸俗主义等错误行为,这就是我们当前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新自由主义西化思潮和新儒家至上思想复辟的最重要最紧迫的学术任务。
注:杨春时著《中国文化转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
二000年十月十二日(字数统计:9,344)
注:全文发表于《理论探讨》2005年第2期,第121-124页。



